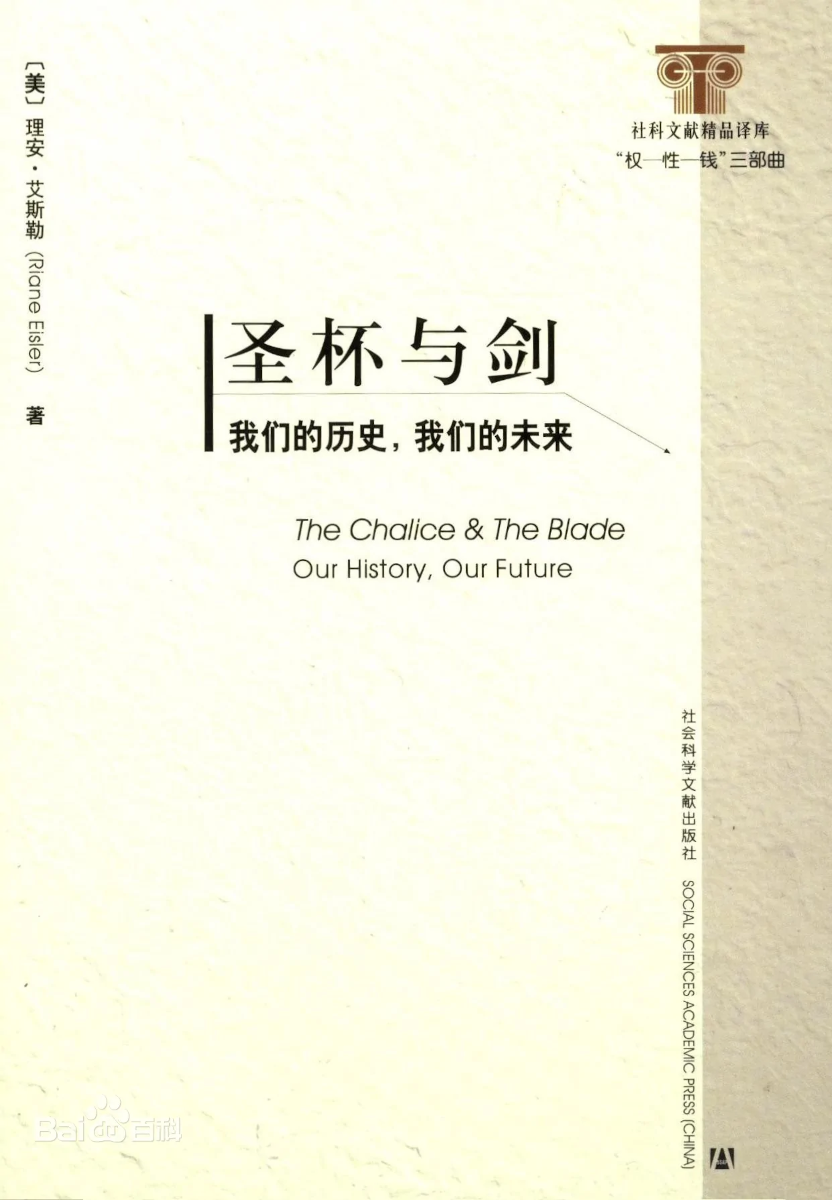《芭比》影评:芭比乐园是母系社会吗?
- 作者:Vava
- 编辑:小舞
- 本文已获授权转载,首发于微信公众号“女泉”
注:本文包含了剧透信息
《芭比》真人大电影自 7 月 21 日全球上映以来,凭借其声势浩大的粉色营销轰炸,成为今年夏季票房的黑马。导演葛莉塔・葛薇也因此成为全球开篇票房最高的女导演,主演和制片人玛格特・罗比也有望在明年提名双料奥斯卡奖项,这都想让我为这些女性电影人欢呼。
然而,对于《芭比》意义的讨论,远不止于它是一部成功的、赚钱的商业大片。更重要的是,该电影引发了全球范围内关于性别议题的热烈讨论。观众们不仅在好莱坞商业电影中首次听到“父权制”这一词汇,还有一些“破防男”们在观影过程中的现身说法也带来的 “4D” 观影体验,成了观众津津乐道的话题。影片中芭比所传达的性别议题态度,以及这种态度是否代表女权主义的问题,也引发了一系列争议和讨论。
作为一个女权主义者,我很难不被各类讨论吸引,我甚至在正式观影之前就已经看遍了全网的介绍和解析,以及电影背后,主创们的访谈和花絮。所以即便该部影片以及 IP 周边创造的巨大经济利益,我预想会按照这个父权制社会一如既往的财富分配方式——进入了男人的口袋,我和朋友们也决定一起穿上粉色的休闲装,踏入电影院,一探究竟。
影片一开始就为我们打造了一座以芭比为中心的 Barbieland(芭比乐园),一个与现实世界性别权力结构完全颠倒的世界:在女性头像的总统山下,这里的政府和最高法院是由芭比所代表的女性领导的,女性从事着律师、医生、飞行员,宇航员等工作,甚至在建筑工地,工人芭比在施工时立起的牌子 Women at work(女人正在施工),都对应了现实生活中路边常见的牌子 Man at work(男人正在施工)。在这里,几乎每个芭比都拥有自己的职业,豪宅,车,宠物,以及各类社交活动。而这个世界的男人们——肯 ,作为芭比后来配置的男友,主要负责引起芭比的注意以及 Beach(字面意义,单纯就是站在沙滩上),且没有人在意肯到底住在哪里。


这种看似颠倒的性别关系,可以被视为对女性乌托邦的想象。在这个世界里,女性看起来拥有着现实生活中所没有的一切权利和权力。然而,这一设定也引发了争议,部分男性观众认为这是一种可憎的母权制(matriarchy),因为他们坚信母系社会中的男性会像父权制中的女性一样被压迫和奴役,然而我们知道并非如此。在 Barbieland 中,肯仅仅是不再作为世界的中心,就足以让他们感到不安而愤怒不已。
我们会自然而然地发问:Barbieland 能算作一个母系社会吗?
幸运的是,母系社会也不全凭靠虚构而来,或者像男性科幻家想象的,是镜像的父权社会。当我们重新回顾被刻意抹去的历史时,我们能发现这样的社会曾经以及现在也真实存在着。美国学者理安・艾斯勒就在她的著作《圣杯与剑: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未来》中,引用详实的考古材料,为我们还原了克里特岛上一个公元前 7000 年的母系社会:
在这个女神崇拜的社会中,如同 Barbieland, 由女性负责重大的政治行政事务和宗教仪式;普遍的高品质生活和规格差别不大的房屋和墓葬,说明这里不存在明显的等级制度和基于性别的压迫;这里的考古挖掘工作中没有发现军事设防工程和侵略战争的迹象,以及存留的壁画和其他艺术作品中也很难找出描述大规模的战争或者奴役他人的画面,说明她们并没有将战争美化成一种掌握权力的象征;出土的精美的陶器和青铜器,其实已经证实当时的人们已经具备成熟的工艺和金属冶炼技术,但她们也并没有像后来的父系文明一样,用于大规模制造毁坏性的武器;岛上的财富也用于改进生活条件,在已发掘的废墟中已经发现了完备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如铺筑过的道路、公路网络、水库,人工喷泉,甚至有非常“现代”的污水排放系统和家庭厕所。这些都在证实克里特岛上这个母系社会中,在女性主导下,生活富足,爱好和平,充满了对生活和艺术的热爱,这一切也都来源于她们对象征着生命的女性子宫 ——“圣杯”的崇拜和对合作伙伴权力关系的践行。

米诺斯壁画上描绘了三个女人。Credit: ArchaiOptix / Wkimedia Commons CC BY-SA 4.0

相对比,古埃及维齐尔·雷希米尔 (Rekhiire) 的坟墓壁画中,约公元前 1450 年,外国奴隶“为底比斯卡纳克神庙的作坊仓库制作砖块”和建筑坡道. Credit: Wikimedia Commons
这些证据也有力回击了长期以来的父权谎言:母系氏族因生产力低下而注定走向衰败,母系社会只是人类历史的婴儿时期。在理安的论述中,这样辉煌的母系社会走向衰退,是因为外来游牧民族利用武器和暴力,血腥掠夺,完成了权力更替。《芭比》里,肯认为父权制的社会是男人和马来统治,而马就如同《圣杯与剑》中的“剑”一样,象征着战争和征服,这种统治模式一直以来在父权社会被反复合理化,美化甚至崇拜。
事实上,直至今日,母系社会并未完全消亡,其身影依然存在于当今社会,例如泸沽湖畔的摩梭人。香港学者周华山在 90 年代,对摩梭母系氏族深度田野之后所撰写的《无父无夫的国度:重女不轻男的母系摩梭》,能够帮助我们更具像化地将母系社会从想象到历史考古,再进一步落实到更真实的生活细节中。
例如摩梭女性当家,意味着女性要承担更多家庭宗族劳动和责任,而男性就像肯一样,相对清闲;摩梭的女性是共同育儿,晚辈会将所有家族内的女性称为阿咪(妈妈),对于生育带来的压力也没有那么多的顾虑;甚至摩梭人的走婚习俗,也并不像早期汉族男性学者认为的那样,是性关系混乱或者乱伦,反而更像 barbieland 里芭比和肯的关系,不需要住在一起,不需要结婚,再亲密也不过是彼此的 “long-term long-distance low-commitment casual relationship”(长期-远距离-低承诺-随性关系),而她们对于父权婚姻中的性别角色和所属关系更是感到不解,比如书中的一位摩梭女性表示,当其他人称呼自己为某人的妻子时会非常不舒适,她表示: “我不是他的,他也不是我的,我是我,他是他,我最多告诉别人他是孩子的爸爸。”
因此,摩梭人社会中女性的主导地位并不导致男性受到奴役和压迫。这种权力在性质上有别于父权那种统治性权力,更多地是承担起让每个人安居乐业的责任,并且女性和男性都不受制于性别规范的限制。这说明了:是压迫创造了性别的差异,而非性别的差异导致了压迫。
但摩梭人长期被父权制包围下,族内男性的变化也与肯突然到了人类社会之后,快速学习父权制社会类似,甚至摩梭人还面临着各个时期父权制的强力干涉和渗透,比如在政治权力上,国家会优先分配政府机关单位的工作给男性,要求当地人必须结婚;外来宗教的渗入使得男性掌握了更多宗教地位;资本用性解放的卖点包装摩梭习俗后,女性遭遇了性化和剥削;这些都让摩梭的肯们真实享受到了父权制下的男性特权。
然后,他们也会很快意识到,父权制的男性之间也有等级制度,如同芭比里小职员那句:“我是这个房间里地位最低的男性,所以这让我变成一个女人吗?”;以及作为少数民族,在种族、学历、技能、财产上的劣势,当文中有一位摩梭男性像肯一般向往去到外面男人统治的世界时,也被其他人无情地评价道:“离开泸沽湖,他只是一个啥都不会的文盲,像个地痞,会活得很痛苦”。所以,当被现代社会无情碾压的时候,很多摩梭男性又会选择重返母屋,享受人与人之间的温情。而无论身处父权还是母系社会的男性如何去思考自己的位置和存在价值,也如同电影中的肯一样,是自己有责任和义务去探索的,而非等待芭比给出答案。
对比 Barbieland 与现实世界中母系社会的相似之处后, 我们也能发现在 Barbieland 这个脱胎于儿童玩具,极尽简化的塑料世界中。将女性和儿童的元素合并在一起,给芭比施加了性别和年龄的双重规范限制。她必须符合关于性别和年龄的固有规范和期望,即接受男性对“完美女性”的身体凝视和成人对“纯真儿童”的智识管控。
比如,芭比的世界看似是一个女性主导的乐园,拥有各种令人艳羡的职业和豪宅,却怪异地迎合父权社会期待中的女性外表:完美无暇的容貌、不成比例的身材、永不落地的脚跟;并且在这个成人视角下为儿童受众打造的“完美”世界中,不存在死亡,压力,衰老,暴力,以及橘皮组织和性都被视为禁忌,她甚至都没有阴道。所以这个优先剔除了所谓危险的,禁忌的,严肃的,负面的内容,只留下观赏性的世界,是与真实的世界脱节的,也注定是一个无法探索真实问题和现实权力的虚假乐园。
因此,当 Barbieland 处于这种被凝视的景观模式时,便将女性面临的具身性和复杂性的问题从芭比身上剥离,也剥离了她作为人的思考和决策的能力,也就导致芭比们在 Barbieland 所获得的权力是失真的,是一种基于设定的循规蹈矩的表演,而非出于自主性。这或许也能解释,为什么肯能够那么轻易地洗脑芭比们服从于他创建的父权制,因为对她们而言,无论是总统、诺贝尔奖得主还是端啤酒的小妹,只不过是又领到了一套新的表演剧本。
这样的 Barbieland 显然是现实父权社会排挤过、阉割过的母系领地,或者说,也在一片在隐蔽实行父权制的领地,对真实的父权权力框架构不成实质性威胁,所以以男性高层为主导的美泰公司(芭比的母公司)也愿意推出更迎合当代独立女性标准的芭比,以及本部电影。当然我们也要承认和赞扬本片的女性制作班底对内容限制的反复协商,才让我们有机会在电影院看到这种以女性视角探索性别议题为主的内容。但是,老实说,荧幕上塑造出的那些蠢萌但不坏的肯们以及美泰男性高层形象,对现实中的男性以及他们的权力和利益根本构不成任何威胁,甚至在铺天盖地的联名和粉色消费主义攻势中,变相鼓励更多现实世界的女性变成自我客体化的“芭比”,走入盒中。
这就是为什么电影中芭比的觉醒、斗争,和出走的每一步都显得格外珍贵的原因。当她被唤醒后,她的身体便不再被局限于完美的芭比状态,而是逐渐展现出真实的女性身体的质感;她在人类社会目睹了衰老的女性,亲身体验了肉身带来的复杂情绪变化和感官感受;她在被男性凝视的目光和侵犯行为中,被迫意识到自己作为性客体的存在;她也曾因为面对 Kendom 的挫败而放弃过自己的身躯,企图等待一个更有领导力的芭比来解救,但随后重新找回自我,意识到自己和自己的身体都不需要他人的认可和允许而存在。
影片的最后,当她穿着平底拖鞋去看妇科医生,象征着那具身体不再是简单而完美的塑料,而是一具有血有肉有阴道的成人女性身躯。她在一次次的出走和探索中,夺回了作为女性、作为人的具身性和主体性。这一切都充满了坚定的勇气和自我认知。
而此刻等待她以及屏幕外万千女性的,又是全新的权力斗争之路,去创建一个真实的、脚跟能够落地的母系社会!
【参考书籍】
- 理安・艾斯勒, 圣杯与剑: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未来[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 周华山.无父无夫的国度?[M].光明日报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