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9十周年 | 专访李和平:我是一个普通律师,走入时代聚光灯下
- 作者:龚江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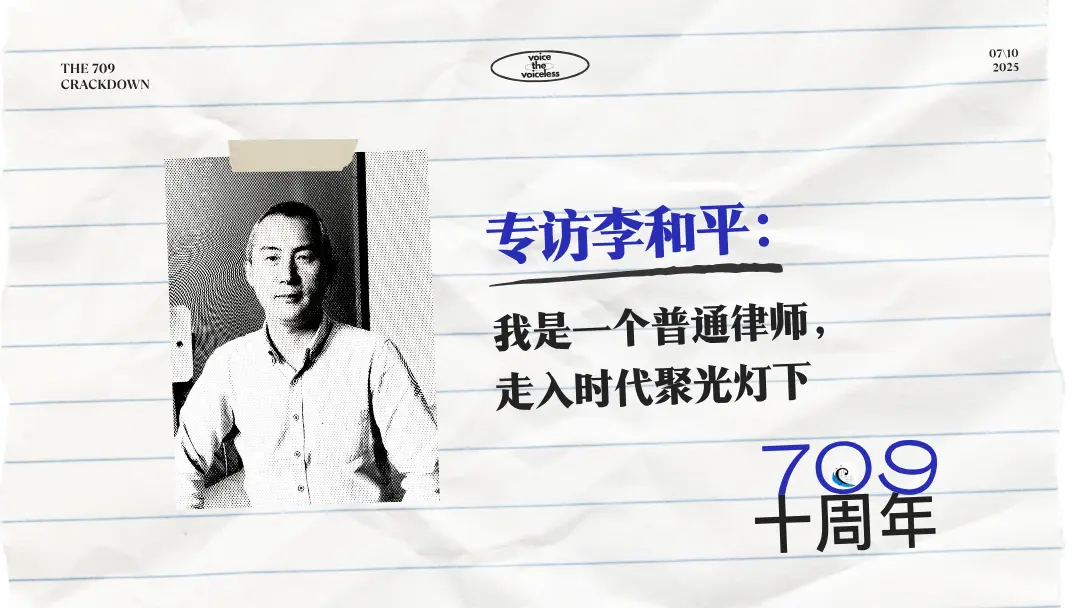
10年前的今天,2015年7月10日,人权律师李和平被抓,在被外界称为“709律师大抓捕”的行动里,他是被捕的律师之一。2017年,在一场闭门审判中,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其三年有期徒刑、缓刑四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
出生于1970年的李和平是中国最早一批活跃的维权律师之一。2003年,他在代理了“新青年学会”一案后,开始走入代理维权案件的道路。接下来的十几年里,他代理了大量涉及异见人士或信仰的政治案件。他从事关于反酷刑的独立研究,他的律师认为这是当局将他判刑的重要原因。
709事件对他的身体和精神造成了严重创伤,出狱八年,他还在努力走出当年的阴影,而一家人的生活没能恢复正常,他们总是被逼搬家,女儿上学也总是受阻。 在709事件十周年之际,低音发布对李和平的专访,谈他的人生过往、从事维权案件的经历、709抓捕和释放后的生活。
“代理人权案件是很自然的事”
低音:你小时候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李和平:(我出生在)河南信阳农村,(父母都是)农村人。印象就是挺苦的、挺艰难的。用中国控诉旧社会的说法,“吃不饱穿不暖”。我们那个年纪都是这样的,中国普遍贫穷、吃不饱。我们属于信阳的大别山区,能看见山,就在丘陵地带。(信阳)实际上是稻麦两熟,主要以稻子为主,也有面。我小时候自己不爱吃面,总感觉(食物)不够。(我有)三个兄弟姐妹,我是老二。高中到了镇上的县高中,我91年参加高考。
(大学)对我最大的改变是,大学给了我时间、空间。(大学里)相对自由,可以自由地乱看书。我(经常)在图书馆瞎看书。真正有印象的是一篇文章《中国农民两亿五》,它把农民进行了区分。我看到这个的时候,有一种被开启的感觉。我在农村的时候,总是感觉自己被欺负、被压制,我们一直是社会最底层。那个时候我们还是要交农业税的,不给,他们是要打人的。你自己穷得要死,别人还要来征税。我的观念都是看书得来的,自己思考得来的。
低音:你是什么时候开始从事律师工作?为什么想做律师?
李和平:97年(开始)。我觉得律师自由一点。那时候,大学生到社会上找工作,是需要有两样东西的,第一个是关系,第二个是钱。我们从农村来的,没有关系也没有钱。那个时候没有体制的观念,只知道要想找一个好一点的工作,(就)需要这两个东西。律师这个行业,相对自由一点,有一点自主性。95年毕业那一年,我就考上了律师证,(后来)做了律师。
因为做律师的时候,不可能一开始就做特别大的或特别好的案子,你做不到,别人也不信任你,就是给你,你也做不出来。你在这里面做出成绩来,别人才会认可你。你刚刚进入,还是一个“小白”。只是后来,随着经验的积累,慢慢的,开始做一些(维权案件)。
低音:最开始为什么会想从事人权案件?
李和平:我在郑州做了三年律师,还算是很顺的,很快我们那边业务都起来了,做得很好。第一,在我们律师事务所,挣钱相对多一点;第二,做业务时很有成就感,很得心应手。后来我觉得我应该到一个大一点的平台上去,起码北京的市场大一点。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如果继续在郑州待下去,资源积累得越来越多,可能就不想走了。所以2000年就到这(北京)来。
实际上(代理人权案件)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在律师圈里做的业务多了,各方面的业务都会来找你。来找你的时候,哪个案子你都要认认真真地做。认真做的时候,你的口碑在各个领域都在传播。有一些案子做起来,获得了某个群体的认同。
我做的第一个能被称为政治案件的,就是北京的“新青年学会”1杨子立的案子。有一个女士(向我)谈到她的老公被警察抓了,现在缺律师。她说她老公叫杨子立。(我曾经)看到有个人写了一首诗,作者就叫杨子立,写得很好,写农民有多苦。我在郑州看到这首诗,就感到就在写我们的家庭,就能产生共情,我读一遍流一遍泪。她竟然说她的老公叫杨子立,我就觉得很感动,(认为)这个人在替我们坐牢。别人替你坐牢,你还不去给他辩护,道义上过不去啊。我想,我就要去给他辩护。
当时我们是十几个人一起吃饭,我说要给他辩护的时候,我老婆就在我旁边。我老婆当时就说,就觉得这下就完蛋了,杨子立替别人呼吁,自己进“号子”了;现在她的老公要替杨子立呼吁,可能也要进监狱,马上我要替他呼吁了。立刻就给在坐的几个朋友讲,那将来我要替我老公呼吁的时候,我的孩子你(们)要替我管。她感觉到很无奈,(但她)没阻止我,也有可能她知道她阻止不了。
(我)和北京的张思之律师、莫少平律师同台给他们辩护,我属于是新手。政治案件一般人搞不了,“颠覆国家政权”这几个字是什么意思,大家都不太清楚。我们做的很好的一点是我们敢于调查取证,他们那些老律师不敢的,(他们)从来不调查取证。
这个案子实际上是八个人在一起读书写文章,聊一些和时政相关的话题。实际上就是几个年轻人成立了一个读书会。国安抓了四个人(新青年学会成员),没抓另外四人。被抓的人,就让他们指控其他被抓的人。后来我们能做到的,就是找到在外面的人。让他们说只是在读一些书,把这些东西都写下来了。他们胆量还真挺大的,除了李宇宙2之外,剩下三人都写了东西提交给法院了,都愿意出庭作证。但是那一天开庭的时候,他们到法院去了,我要去叫他们进来,法官不让他们进法院。
低音:这个案子过后,你是不是更多代理更多的类似案件?
李和平:(维权案件)不是说想代理就代理,也没有谁真的想代理。这种案子都是赔本的,你投入了很多时间,实际上你根本没有收钱,免费(代理)。付钱了也是几千块钱,很少,象征性的,完全不够。和其他案件相比,投入的时间要多几倍,投入的工作量也大。从经济的角度考虑,没人愿意做这种案子。
我为什么研究酷刑
低音:开始代理维权案件后,受到过什么压力吗?当时有什么感受?
李和平:05年,陈光诚3的案子。05年的时候,他在山东临沂搞计生(计划生育),(对抗)很激烈。他到北京来,寻求法律帮助,我们这边有时候给他一些帮助,也有时候给他一些钱。因为他特别穷,眼睛又不好,我们也支持他一些,免费给他一些帮助。
有时候开新闻发布会,那时候所谓的新闻发布会,其实就是把记者请来说说话。警察也是很不愿意出现这种情况,他就想把这事搞没。有一次陈光诚就想开新闻发布会,我也要去,警察就想拦住我,不让我去。国保过来(对我说)不能去。我原来对国保没有什么概念,不知道里面还有个“政保”部门。我没有同意不去,他们说,那你去不了,他们就在(我家的)门口布置几个人,不让我去。
她(我老婆)早就知道有这些事,因为我们这边经常见到这些人(指便衣警察)。有一些(上访人员)到我们这来给我讲他们的上访经历,讲这些事的时候(她都在)。我当时感觉,这怎么可能呢,警察怎么能违法呢。(我)不相信这些事。
陈光诚这个案子,牵扯的人挺多的,律师也挺多。很多律师去(陈光诚家)会挨打,就衍生出若干个和陈光诚这个案子有关的案件。我们是其中的一部分,最开始我们去的多一点。他告公安局的时候,我也去过。我们去的时候,警察也拦我们,截我们的车。还有我们去给盲人讲课,这些我们都做过。我感觉到这是一个(大的)事项,我们是事项中很小的一部分。
低音:你是怎么平衡代理人权案件和家庭之间的关系?
李和平:这是一个鸡肋的事情。04年或05年,那时候警察逼迫高智晟逼迫得特别紧,他走哪警察跟到哪,甚至警察到他家里面。因为我跟高智晟关系好啊,而且做的是同一类事情,感同身受。我回来也给我老婆感叹了一下,说他们这样逼迫高智晟简直太坏了,高智晟为了公义受这样的待遇,太过分了。我老婆说,他哪是为了公义,他只是为了自己的名利而已。我就很非常生气,我老婆不敢讲话。这就引起我的深思:我到底是在为公义,还是为了自己的名利?
(我认为)这需要仔细琢磨,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多年。我(认为),它们之间(不是)非要选一个,这两个(公义和名利)之间是有区别的,但是在中国人心中是区分不了的。边界在哪里?这个问题,我至少想了三年。后来我在美国和王怡牧师聊到这个话题,他给我讲两个之间的区别,(他说)那些名誉、荣耀不是人的,是上帝的。人不能把这些东西想的太高,不能把这些东西想成自己的,你只是个管家而已。
我们(李和平和妻子)有一个很大的冲突。她就离家出走了,但她后来又跑回来了。我就自己反思了,反思这个问题本身。实际上那个时候,我的妻子也不理解,她也区分不了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当时我认为自己很公义,不希望别人做出一个否定的评价。比如说,我做的这些事,就像共产党做的事,很神圣的一样。但实际上,我自己的灵魂深处,有暴虐的一面。
低音:介绍一下你代理过的其他案件。
李和平:最重要的就是法轮功案件。我在07年的时候,就给法轮功辩护了。(有一个案件)一家三口都是法轮功(信徒),当时他们一家三口上《焦点访谈》,上了三次。《焦点访谈》的意思(是),这家以前不是法轮功的(信徒),生活很好;后来他们信了法轮功,生活不好;最后政府不让他们信,生活又好了。实际上,中央电视台采访的时候,他们一家三口讲的是另外一个故事:开始的时候生活不好,信了法轮功之后生活变好了;政府打压之后,生活又不好了。新闻完全颠倒事实,他出来以后,把自己的经历录下来,发到海外网站上,那警察就生气啊,把他们一家三口都抓了,我就为他辩护。
那个时候给法轮功辩护是很危险的。我做了一个相对来说很彻底的辩护:“宪法至上,信仰自由”。这份辩护词写出来以后,成为这个领域的一个范本。当时做这个辩护的时候,想的是可能当时就要坐牢,但是到了十年以后才坐牢。并且在709的时候,这个辩护词他们拿出来,一点点问我为什么这样辩护。
低音:你认为立刻要坐牢,为什么还要做这个案子?
李和平:因为我们是做法律的。按照法律就是这样,这才是真的。我就应该讲真话。我觉得我讲的就是事实,我就是按照法律讲的,完全没有超纲。并且我们上面还有一个大抬头呢:宪法至上。信仰自由就是(宪法)三十六条,我说的这一切都是在法律范围之内的。
低音:你当时为什么想研究酷刑?
李和平:最开始的时候,中国没有酷刑这个概念。中国讲的是“刑讯逼供”,“刑讯逼供”这个词是不能和国际接轨的。中国在1986年加入了《禁止酷刑公约》。12年中国刑事诉讼法修改,有一个非法证据排除,任何人不能自证有罪。酷刑证据就是非法证据,这就是研究酷刑的必要。我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研究酷刑。
当时我是想做一个法律界的研究4,实际上法律圈最最缺的就是这样的研究。当然政府对这方面非常反对,不想让律师(研究)。当时我就想先尝试一个,(组织)律师开会研讨这个话题。《禁止酷刑公约》我们可以学习,看看国际上的概念和中国的概念的区别。
原来我们中国人,包括很多律师、法官、检察官,大多数人都认为,对这些被羁押人员打一打(是正确的)。为什么呢,他不老实,你不干他们,他们怎么能配合呢?我们这些律师开研讨会的时候,(大家)都这么认为,大多数人都认为要打,因为在中国,你一进校门,它就讲“法律是统治阶级的专政工具”,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暴力工具,法律是统治阶级的意志的表现。要是按照这一套来讲,哪还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啊。
酷刑不对,法律上违法,但是为什么不对,它的价值在哪里,说真的,很多人说不清楚。实际上,我们如果对某一个人能够进行酷刑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就是说,任何人可以被以任何罪名关押。对某一个人进行酷刑是想保护自由人,但是实际上不是,酷刑是说,你用这个逻辑,实际上可以把全社会的人都打了,并且搞成你想要的罪名。
“做刑辩律师,去坐一下牢,是有益的”
低音:你认为自己为什么会被卷入“709大抓捕”?
李和平:(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律师而已,只不过做案子认真了一点。后来碰到了一些业务的增长,关心到一些人权的问题。关心多了就涉及到一些群体,他们有一些共同的诉求,例如信仰、人身权利、住宅权,(有)一些共性。再去为一些案子辩护的时候,就(有)一个群体关注这个案子,无形中,这个案子的影响力就上来了。(我)又是这个案子中的参与者之一,也会成为别人关注的主角。
这样,我们走到了时代的浪潮、时代的聚光灯(下)。在这个时候,我们在法律领域里被凸显出来了。我们的客户认识了我们,表现在很多案子来找我们;不喜欢我们的人就打压我们。这就形成了两股力量的博弈。
在这种情况下,认为我们替他们讲话的、维护他们权利的一些人,他们对我们的行为很赞许,认为我们维护的法律保障了他们的权益,是中国所需要的;另外一些人想来侵犯老百姓利益,向这个群体进攻的时候,我们就成为这个群体的挡箭牌。它要突破我们,它就想把我们给碾碎。想打压弱势群体的人是国家公器的掌控者,他们可以利用国家权力来做一些事情。15年,矛盾足够激烈了,就发动了709事件。
低音:讲讲在709大抓捕时的经历。
李和平:(我在7月)10号被捕。我到我的办公室,刚停好车,刚下来,感觉有一二十人,穿便装,有人照相。他们可能有一些人要到我们(办公室)那边,抄我们的办公室,另外一部分人从那个地方回到亦庄,我的家。我们在三元桥这边,我女儿也在我车上。我们又开车回亦庄,他们开车,我坐在我的车上。在亦庄,我把女儿给了我老婆,他们就把我抓走了。
我就(被)带上黑头套了,没有(出示任何法律证据或者文书)。在那种情况下,反抗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不知道(被带到了哪里),开始可能在北京,但是我不知道。
前面六个月,对我是单独关押。他们有一整套体系、流程,很成熟的一套体系。(我被)换了好多个地方,我不知道这里面是(哪里)。(我被关押的地点)是一间房子,可能是楼房。我不知道几层楼,给我带到电梯里面。就有一面墙,周围全都是软包,有几个摄像头,有的房间里有卫生间,有的房间里没有卫生间。窗户什么都给密封起来。
我就不太想详细讲这些东西(指酷刑),在我的眼里,这些东西已经没什么意义了,因为中国的这样的事情太多了,(对)我的做法和(对)别人的没有多少差别。因为我是律师,我以前研究酷刑,自己又受酷刑,反差很大。我之前做酷刑研究的时候,是想象的出来:不就是打你,不让你睡觉吗?不让你吃饱吗,冻你吗?实际上远远不是。因为你自己真正的体会和研究别人的痛苦不知道相差多少万倍。只有自己真正去体会过,那才叫感同身受。做刑辩律师,去坐一下牢,是有益的。
例如不让你吃饭,或者给你吃很少很少的饭,饿你。你可能一天吃少一点,一天吃少一点,到后面你没有力气。还有就是让你吃药,第一天让你吃药,(吃药后感到)困,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从早上起来,一直打哈欠到晚上。
中国对关押人员的酷刑就是要让你驯服,让你驯服了之后,他要什么你给什么,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这个案件就做成了。
这里面(我和当局)是有妥协的。他们要求我自诬说我有罪,我不认罪,我说我没有罪我不自诬。他说我不需要你自诬,但是只要你不去辩驳就行,你让律师给辩,你别说你无罪。(我同意了。)我就说我们一切都是合法的,这样的话可以说,但是不能说我无罪。
他们完全不管,因为这些人完全就是流氓。(我)要求为自己聘请律师,他们就说,你要求一个律师,我们就抓一个律师。我说挺好的,那就你抓吧,我就把好几个当初很出名的律师都写上去,你抓吧。还有后面填了一句话:或者我妻子作为亲友辩护人。但是(当局)都不让他们来(为我辩护)。
低音:你被宣判为缓刑后发生了什么?
李和平:(当局)又给我送到天津盘山,公安局的一个培训中心,到那里待了十天,把上诉期搞过去。那个时候瘦得太狠了,出来之后就像从集中营出来一样。我估计那十天至少一天要长一斤。(我)自己有一个房间,里面有一大批国保。鸡蛋啊,粥啊都有,不是什么大鱼大肉,但是你想吃大鱼大肉也是能搞得到的。
有个程序,从天津盘山送到“阳光中途之家”,从看守所或者羁押场所送到司法局一个中转站,在那中转一下,再给你戴上一个电子镣铐,再给你带回去。我不同意,后来没戴成,后来和他们僵持好长时间,最后没有(让我戴)。司法所把我送到马路边上,让我自己进去(回家)。
她(王峭岭)说,她不相信我回来了。我当时是迷糊的,人在外面是晕的。我出来的时候,我能感觉到,我的话达不到(我想表达的内容),我们之间是有隔离的。(我)花了一个月时间,才逐渐了解这些事情,把这一段断档的给补上。
当时我的门口有几个人跟着。门口有几辆车,他们七十多人。盯我的人告诉我,他们有一个保安公司,领了这份差事。他们直接告诉我的,保安里一些人想法不一样,有些事就直接告诉我了。
“没有什么可以后悔的”
低音:从709被抓捕到今天,你是用什么办法疗愈自己的?
李和平:时间。因为它给我的伤害太大了。
现在精神状态比刚出来的时候好一点了。不是隔阂,是一种奇怪的感受,在看守所处于一种防守状态,好像自己的边界被压缩了。
回来好长一段时间不能看书。看守所里面不能关灯,把眼睛搞坏了。警察对你进行恐吓嘛,限制、欺骗,什么手段都用,怀疑增多了。没有进去过的人,可能想着这些人进去也就两年,很快就出来了嘛,有多大事情;实际上,人在里面经过酷刑之后,酷刑的时间和外面的时间不是一个时间。人在那种严酷的环境下,会感觉到度日如年。在里面待六个月,在关押的人眼里,六十年都有可能。
低音:你最近又经历了“逼迁”,可以分享一下经历吗?
李和平:2023年七月份的时候,他们不知道什么原因就要来搞我。在这之前,他们已经找我,房东总是想办法要我们走。我们接到消息,我们在顺义想租到房子是不可能的。派出所把中介叫到一起开会,把我们的名字给他们,这个人在顺义这个地方租房子,是不能租的,谁租的找谁的麻烦。他们有一些中介的人,因为我们老找房子,也有一些朋友,他们就告诉我了。
我们在顺义那个地方租了一个房子,我们把东西已经搬进去了,房东去在小区备案的时候,派出所说不能把房子租给我,他就赶快过来把房子的钥匙给换了,不让我们住。(合同)签了,钱都给了。反正到最后的时候,我们就搬到通州宋庄这个地方来,警察又跟过来,逼迫的又让我们从这个地方迁走。他们就让房东把我们大门也给拆了,玻璃也给砸了,很多事。可能从我回来,到去年七月一日从宋庄搬到这个地方来,我们前前后后搬家,搬了可能有八九次。
低音:你的女儿一直没有学上,可以讲讲怎么回事吗?
李和平:当时我那边一出事(2015年被抓捕),这个中心国际的幼儿园,本来她该上一年级的,学校里就说不能接收,因为派出所那边不让接收。房东也被警察要求不能给房子租给我们。我在被抓的时候,我老婆主要精力在为我呼吁,小孩都顾不上了,顾不上了小孩,就送回老家一个月。她一个月后就把女儿接回来了。
我女儿因为长期的这种逼迫,情绪非常糟糕。她就很焦虑,不愿意在北京了,不想回北京。并且之前我们也是想出去(离开中国),到海关,去了两次都被拦了。原来我不想离开(中国),现在为了孩子上学的事,我可以离开啊。
低音:你后悔之前做的事情吗?
李和平:没有什么可以后悔的。你后悔有什么意义呢。这就是每个人的命运,就是上帝让你来做这个事情。
低音:你有什么想对妻子说的话吗?
李和平:说什么好呢?有时候说感谢的话,说不出来,现在我对我老婆肯定是很感谢的。说真的,就是舍命来救我,没有她的这种付出、顽强的抗争,709有可能就被他们搞的无声无息的。我要感谢我妻子,包括李文足她们(其他709律师的妻子)。她们是一个群体,但是他们这个群体最终的力量来源还是上帝。如果没有基督教信仰,她们也走不到一起来。所以基督教信仰真的特别重要,没有这个一切都做不成。因为有上帝、有基督教的信仰,她们可以一起不退后。
-
“新青年学会”成立于2000年5月,是由5名应届毕业生自发组织的学习小组,后有另外3人加入,主要讨论当时的政治、民生等问题。2001年遭国安部门突击绑架,后4名成员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2人获刑8年,另2人获刑10年。 ↩︎
-
李宇宙,新青年学会成员,随后被认定为奉北京市国家安全局之命前来卧底的内鬼。他按照国安指示揭发其他成员并担任证人,使部分成员被判刑。案发后,李宇宙逃往泰国,并对媒体披露了自己的角色。 ↩︎
-
陈光诚,山东盲人维权人士,因自学法律为村民维权被称为“赤脚律师”。2006年,陈光诚因揭露山东暴力计划生育政策而被判刑,2010年获释后遭软禁。2012年4月,陈光诚闯入北京美国使馆寻求庇护,随后流亡美国至今。 ↩︎
-
2014年,李和平开始从事关于酷刑的NGO项目。他的律师马连顺认为,在关于酷刑的NGO项目中接受境外资金是他日后被判刑的重要原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