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遗忘 E13 | 中国女性研究开拓者李小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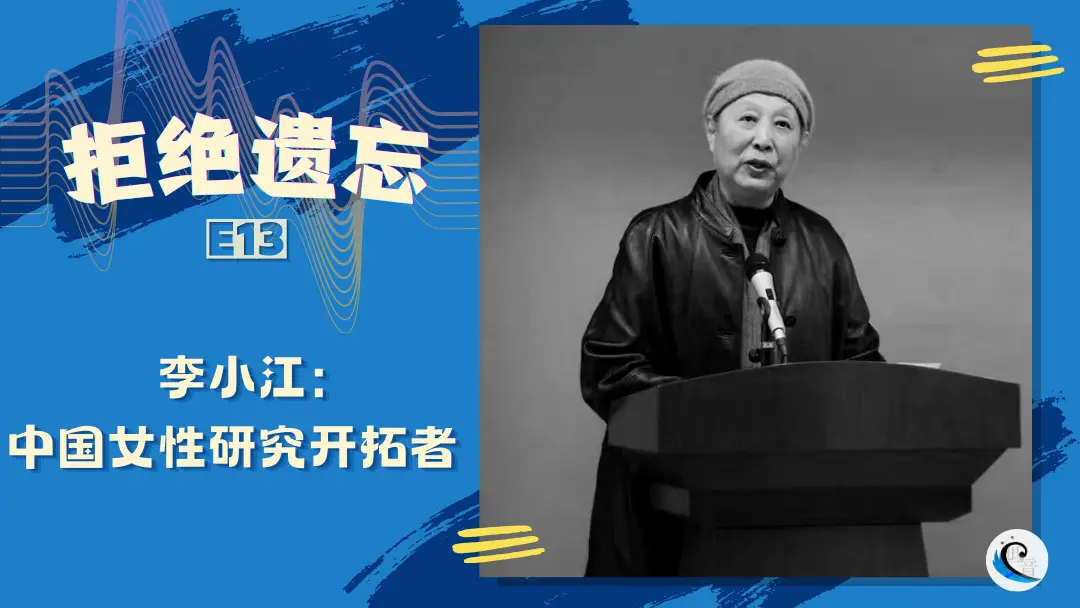
本期简介
1995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是中国第一次承办的联合国国际会议,打的便是“妇女”这张牌。北京“世妇会”已经过去30年,这些年里,中国的女性议题得到前所未有的丰富,不论是妇女研究的方向,还是女性主义的内涵,在具体的实践上都已经大不相同。
随着近年来微博女权在网络上的活跃,米兔运动在中国引发轩然大波后,“女权”这个词汇更为人所熟知,而“妇女”这个词似乎逐渐淡出讨论。但当我们追溯历史,“妇女”比“女权”,更早进入中国有关性别角度的社会改革话语中,许多女性学者在这一领域做出了巨大贡献。李小江便是其中重要的代表。
对年轻一代的女权主义者来说,李小江可能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她从80年代开始,致力于的中国妇女研究,为我们如今理解中国语境下与性别相关的词汇、运动,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2025年2月12日,李小江老师因乳腺癌于大连逝世,时年74岁。低音想要给大家讲述她的故事,讲述这个用自己一生的见闻去理解、诠释何为“女性”的一名学者。
参考阅读
- 《“主义”与性别》 李小江对话上野千鹤子
- 《开拓中国女性研究的人,不想当女性主义者》谷雨
- 李小江老师书信回忆录(序)I 《华人家园与天下》唐凌
- 《走向女人,反省平等 》李小江(《女性乌托邦:中国女性/性别研究二十讲》节选)
- 《妇女解放?女性乌托邦——女性主义的历史命运及其学术作为》
一、“男女都一样”的政治,“男女不一样”的现实
李小江出生于1951年,在毛泽东口中,这是一个“男女平等”的时代。
小时候看着报刊杂志里“铁姑娘”的故事长大,李小江是一个“不喜欢梳头,不爱穿鞋,喜欢爬树、打弹弓、光着脚满地跑”的假小子。在回忆这个时期的中国社会环境时,李小江提到为什么中国和西方的性别文化不一样,她说,“想做男孩子,你去做就是了,没有那么多阻力,甚至还会受到鼓励。上学期间,没有感到什么性别压力,下乡做知青也一样,没人特别照顾你”。对于成长在那个年代的女孩来说,男尊女卑的传统似乎早已打破了,“许多女性进入传统男性的领域,那时候出现了新中国第一位女拖拉机手、第一位女汽车司机、第一位女厂长等等。”
1975年,李小江结婚,两年后,她生了孩子,用她自己的话说,自己开始掉进了“女人的陷阱”。她发现,“男女都一样”的说法和她的现实相距甚远。李小江在《女性乌托邦:中国女性/性别研究二十讲》中“走向女人,反省平等”一节中说,“你谈不谈恋爱?婚姻生活中你和丈夫怎么相处?家务谁去承担?孩子的事情谁来管?”
去年,腾讯谷雨实验室发表了一篇关于她的人物报道《开拓中国女性研究的人,不想当女性主义者》。文章里写到,做了母亲的李小江疲于奔命,读研,学业、孩子、丈夫、家务,所有事情都在争夺她的时间和精力。她在访谈中提到,“如果还以过去那种独立的行为方式和价值标准要求自己,我感到处处是障碍。但是要我放弃,心里也一百个不愿意。你在这时候才感觉到自己掉进了一个陷阱,一个历史的、关于女人的陷阱。”
李小江不愿压抑自己真实的感受,选择了“自己去寻找女人的答案”这条道路。
在七八十年代的中国,到哪里去找女人的答案?怎么去找女人的答案?在当时,没有人有答案。1986年之前,中国没有一个专门研究妇女的机构,没有一份妇女理论刊物,也没有任何一所大学设有专门的妇女学教学岗位和学位。
二、寻找女人,在女人的故事中追问“我是谁”
李小江在2016年出版了中国女性/性别研究合集《女性乌托邦:中国女性/性别研究二十讲》。在这本书里,她讲起自己的人生是如何跟妇女研究连接在一起:
她自小对历史和哲学有浓厚兴趣,但她发现,经典哲学理论中没有女人的身影。她说,“女人”在历史上整体性地缺席,在曾奉为圭臬的历史和哲学经典中的缺席,对她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冲击。出于对男人书写的“历史”和“哲学”的不信任,她想要去反叛,想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去看到和教科书中不一样的,真实的历史。
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女性在现实生活中面临的新困境逐渐显现,而“男女平等”的政治主张掩盖了这些问题。例如,1980年,“感情破裂”作为法定离婚理由被写入新的《婚姻法》,这个法条看似增强了女性在婚姻中自主性,但却没有为离婚后陷入经济困难的女性提供解决方案,更加暴露出婚姻与经济地位之间复杂的关联。此外,女童失学、女工下岗等问题,也并没有因为法律上的“性别平等”而自动解决。
李小江在2016年题为《妇女解放?女性乌托邦——女性主义的历史命运及其学术作为》的演讲中还举了一个例子:
就比如说平等,在新中国是立国的原则,可是一直长期难以落实在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中间。我们今天不愿意讲,但一定要讲的是什么?是城市里的妇女的社会地位,高于所有的农民。我想说所有的,不管你在城市里没有工作,户籍上都给你有保障,你在这个方面,在城乡二元结构上,中国城市妇女在地位上高于(他们)。在这种情况下,男女平等的诉求不可能像西方女权那样的单纯。也就是说,缺乏了社会公平的基本内涵,任何貌似平等的立法,在实施中间都会打折扣。这也是女权主义在中国社会缺乏成长空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我们对“妇女”的讨论,是否足够关注到她们具体的生活处境,而不仅仅是围绕政治理念展开?对“男女平等”的诉求要怎样才可以更接近人们的生活?作为一个在地的学者,李小江希望通过“地缘”的方法论,来讨论这些现实的问题。
她索性走了出去,在工厂,个体摊贩,婚介所等各种地方做一线社会调查。她其实很早就退休,开始过一种隐居的生活,但直到生命的最后阶段,她在还在大量整理女性口述资料。2003年三联出版的《让女人自己说话――20世纪中国妇女口述史》四册从书,就是李小江将妇女史和口述史联结在一起的成果。为了做这个在当时算得上是最大规模的女性口述史研究,李小江走访大江南北,采访了包括抗战时期的女性军人、普通农妇、慰安妇等上千名女性。
即便在确诊乳腺癌前,她还在陕西、江西、云南等地做了很多年的田野调查,采访了许多农村妇女、少数民族女性,女手工艺人,以及佛教女性出家僧侣。现存于陕西师范大学内的妇女文化博物馆里的大部分展品,都是李小江在做口述史时期亲手收集的。她步伐不停,到访了更多的地方,走进更多女性的生命,但与此同时,她也强调要不断回头,重新挖掘这些历史素材里的宝藏:
有一点是要做的,就是我们要回头,回头。别老说往前走,往前走,我们后头所有的东西,我们的垃圾没有清理,我们的遗产没有一条一条理出来。一天到晚是前头走,前头走,你靠什么支撑着你啊?所有我们的研究必须从重返历史开始。
1982年在河南大学西欧文学系研究生毕业后,李小江在郑州大学中文系任教。
1983年,她发表了《人类进步与妇女解放》这篇理论文章,大胆提出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性别讨论的质疑,提出“阶级解放不等于妇女解放”的观点。这篇文章让她的“妇女研究学者”身份,在学术界得到肯定。
1985年初夏,李小江把自己对妇女研究的热情,从理论的世界带进了更多人的现实。她与河南妇女干部学校合作,第一次开设了面向社会的“女性自我认识”讲座。这些讲座的观众里,有很多是当时的妇女干部,和一些受过教育的知识女性。
1985年秋天,李小江在郑州大学中文系开设了“妇女文学”课。开设这门课,她遇到了重重挑战。系学术委员会提出阻挠,说开“女作家研究”可以,做“妇女文学”不行;课上,她遇到男同学调侃,说“李老师什么时候开男性文学?”;学术交流的场合,她被其他学者挑衅,说“文学还能分性别吗?跟男女厕所一样了”。她还遭遇了政治压力,有人质疑她,“你把妇女抽象出来是什么企图?要搞资产阶级女权主义吧!”
1986年,河南人民出版社的编辑陈智英找到她,问她能不能编一套和妇女有关的丛书。李小江说,要编就编一套妇女研究丛书,如果由她来做,这套丛书将不会是以女性为噱头的畅销书,而是一些可能赔钱的学术著作。这套“妇女研究丛书”在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陆续出版,共17册,白色封皮,装帧朴素,从妇女文学,性的社会史,上古文化中的女性根源,妇女运动,古典诗词中的女性和女性审美等各个不同的角度,诠释了李小江心中那个更真实的有关中国女性的历史。今天中国妇女或性别研究领域耳熟能详的名字,比如潘绥铭和戴锦华,都曾出现在这套丛书里。
李小江不仅用很多时间寻找女人,还不停地在女人的故事中追问,“我是谁”。
在一些访谈和与其他学者的通信中,她屡次提到对于权力,“主义”和“政治正确”的警惕。 在接受谷雨访谈时,李小江分享了一件事。在主编“妇女研究丛书”时,出版社曾希望邀请一位妇联的官员来做顾问,她谢绝了这个提议。在后来出版的另一套丛书里,她为自己的行为做了解释。她写道:“为了保证让女人自己说话、避免不必要的打扰和干扰,项目执行期间,没有任何官方机构介入,也不曾得到官方资助。”
她对做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的坚持,和对政治、名声的警惕,来自于自己和家人在“文革”中的经历。她说,“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就想知道到底是什么东西决定了你的人生命运中什么是红、什么是黑,我们昨天还是接班人,今天就是黑五类,又是为什么?”在她日后的妇女研究里,她非常强调不为某个群体,或者女性整体“代言”,并且与“女性主义”讨论中的“政治正确”保持距离。
性别研究学者唐凌为李小江《华人家园与天下》写了序言,里面提到了李小江和她在书信往来时对这个话题的交流,从警惕“主义”展开到如何做一个“踏实”的学者。李小江说,“‘小确幸’之幸,不在幸福之大小多少,在‘踏实’,即自己对个自命运的自主把握。尤其是知识女性中的佼佼者,要紧的不是拿基金会的钱专事救世主之职救助所谓弱势群体,而是自食其力,做好自己。不是用放之四海的那个‘正确’去绑架他人,而是慎独自律,守住本分…出现了问题怎么办? 群策群力,该是‘问题中人’站出来为自己说话,而不是让那些专事‘打抱不平’的人自我赋权强行代人发言。生在红色中国,经历过文化大革命,见多了左派领袖和领袖欲爆棚的革命者,因此我最怕的就是‘代言’,最要警惕的就是所谓‘代表’。 ”
除了“妇女研究丛书”,李小江还参与组织翻译了一批女权主义经典著作,包括《第二性》和《女性的奥秘》。李小江是最早向国内介绍女权主义理论的学者之一,也是在那个年代,少数强调做妇女研究同样要注重理论发展的学者。这两本书在当时的中国不太受欢迎,这让李小江开始思考西方的女权理论和中国妇女现实之间的割裂。她觉得,和女权主义保持必要的距离,也许只有这样,才能够和中国妇女真实处境靠的更近一些。
1995年世妇会召开,李小江受邀,但拒绝了参会。之后,李小江的身影开始慢慢淡出各种学术场合。就像她在2016年的演讲中说的那样:
你说XX给我发了一个函,问我是不是愿意来录像。其实我非常不愿意做这些事,但我这次答应了,为什么?我就想讲一讲,讲完以后,我就回山里去了。你们随便访,就是这样。我就把话讲在这边。将来有很多东西,大家去阐释,批判也好,支持也好,没关系,关键是我们要把思路打开。
她的确出现得更少了,可21世纪以来仍然可以看见她不断的知识产出,比如于2000年出版由她主编的《身临“奇”境:性别、学问、人生》,她邀请了一些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为妇女研究和妇女运动作出贡献的人写下自己的人生故事,容纳了不同的学术观点。她还分别在2004年和2019年与东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上野千鹤子对谈,聊中日两国的女性问题和《超高龄化社会中的福祉与性别》。
她在这片土壤上抛下了种子,又把空间留给了后来者。
三、“仰望星空、心向远方”
2007年李小江确诊乳腺癌,手术切除了一侧乳房,但2023年乳腺癌复发,当她察觉时却已经进入晚期。她从大连大学退休后,长期独住在大连附近一个叫庄河的城市,过着不被打扰的生活。在发现癌症进入晚期后,她从庄河搬回大连的一家疗养院,为了方便治疗,也为了在生活起居的琐事上节省时间,好把生命中最后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给口述史资料整理和研究。
在面对后辈的学术请教时,李小江常说,要“在代际交接的历史经验中找到共同感兴趣的话题”。2019 年新春,她给学术圈的友人和向她请教的学子,寄出了题为《华人家园与天下:致所有“仰望星空、心向远方”的年轻朋友》的信件,后又跟上四封。信中徐徐道来她的人生经历和学术感悟,字里行间流露着她的严谨,温柔以及对后辈饱含期待的情感。其中一封信是这样写的,“我很清楚,对华人或对中国人来说,越是“仰望星空、心向远方”的,越将深陷困境难以自拔;身为女性,更是多出了莫名的困窘难以超越…我知道,只有认真对待人生且对社会有担当的人,才会这样思考如此困惑——仅此而言,没有代沟,我们是一类人,心思因此是相通的。”
她在2016年的演讲中还谈到,在全球化背景下,女性议题如何“越界”,和其他全球化议题产生联系:
多年来我在中国做妇女研究,大家知道的,我是从来不戴女性主义帽子的。并不是要刻意作对,而是基于不同的生存环境,历史道路,可是今天呢?情况有很大的变化。全球化背景下,社会议题基本上都是越界的。传统议题以新的面孔出现。女性主义也将带有鲜明的全球化性质。无论在哪谈论女性,谈的都不将是一家一国的话题,而是全世界女性共同面对的问题。这些问题看似新鲜,说穿了,无非是女性的生存和发展,与历史上的问题一脉相承。所以我总讲,思想可以传承,经验不可复制,思想之花长新,理论之树常青。我认为新一代,我们今天谈到的后解放世代的女性,将会在自己的经验中发现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尝试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我相信,在需要的时候,她们会像我们当年一样,反身回顾,将历史资源用作未来发展的基石。
李小江在其中一封信件里说,“学术世界里,精神上的春天与四季无关,只在心田。”
她的精神也是如此,在我们的世界四季常青。
您也可以在这些平台订阅“低音播客”。
